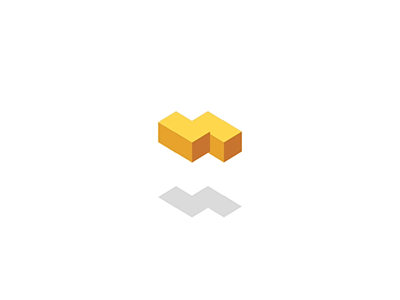《移动》,1951年,Pierre Alechinsky
“当人们开始抛弃他们造的神。”
多年以前,不知是几年以前,当河城不过是连墓地都没有的小渔村的时候。
“渔村”一词不知道是一个功能上定义的还是地理概念,由于当时的河城甚至没有鱼竿,先当地理概念来用了。
每年到了五六月份,山岗子间就会因为连绵不断的下雨变得泥泞和没有生气,天一阴沉,雾霾霾的世界就使得人们无法耕作,整个河城镇变得死气沉沉。受够了这样的周而复始,食物不够了,或者只是他看惯了山峦叠嶂想看看海,江渝提出了移村。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人们被他说服了,说服河城人的,是他宽肩硬气的体格,是蓬乱而花白的头发和眉毛下的,在高高的颧骨和鼻梁中间挖开的眼睛,总是很坚定,不容说二。也许是他做的事,或许都不是。很显然,我没见过他的样子,以上的描述的都是现存的雕塑,当然制造者也没见过他什么样子,也不需要见到,毕竟领袖只有这一种长相。
即使选择的正确性放如今已经很难评判了,但今日的河城人是以正确默认的,不然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失去了合理性。他是现在河城的祖先,河城博物馆的第一个馆当然是他的纪念馆。山腰上,公园里,图书馆大堂中,有时躲在高山上的某一个角落里,每一处,肉眼可及的地方都有江渝的画像,雕塑。河城与江渝似乎是捆绑的两个词汇。河城人有一句话,“在河城,你可能看不到一个人,但是不可能看不到江渝。”
在反对移村的一摞子人中有个叫李赖子,准确来说是被后人叫做为李赖子的,他本名是什么在图书馆中都能查到,我懒得去翻阅,没有人在意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因为在人们心中已经有了为他塑成的形象,小丑不也只有一个模板吗。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批人,一类人。也许是个精瘦小子,邋邋遢遢,没准是个黑秃胖子,赤条条裸着上身......
他的地和很多人一样,都在那山沟里,他反对的很激烈,好像移村就等于革了他的命似的。当然由于过去很难还原,我的叙述也不过只是一扇窗罢了,窗后和窗子上错综复杂的蜘蛛网有待您去想象了。
不过一移了村土地确实就得重现分配,新地方的土壤当然属于新的开拓者,没有任何一个拥有现有资源的人想凭白无故失去它。但,能有什么资源,这村只不过就二十几座木头房子。哦,也许是那座孑的祠堂,那座祠堂倒是蛮大蛮派头的。李赖子的所有条件都在反复阐述一点,即没有人会正眼瞧他,但不尊敬他爹可就少了。
老李曾是孑的使者,多亏了老李向孑祈福,才使河城风调雨顺,节气年年和老李预言的别无二致,事事顺着河城人的意愿来,夜晚没有骇人的狐狸叫,一切不公都会在向孑祈福后烟消云散,孑也常常会下达他的旨意,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一个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即使这个人是莫须有的。老李死后,没有人懂得这些祭祀祈福之礼,这一重任落到他李赖子的肩上。
“要移村了。”徐磊夹起了一颗棋子,他皱起眉头,边摇头边说,“不过是大海叫江渝搬过去的,还是大山要把江渝赶走,我还拿不准。”
“没准是他把大海搬过来呢。”老樟树洞里,郭辉在移村告示旁撸着袖子,笑了笑,又假装看了个走眼,故意输给了徐磊,他从来没赢过老徐,但他自己知道他没一把输过。
过了晌午,赖子看到了告示,“郭叔,这什么时候的事?”
“赖子,过来,叔教你如何下棋。”
李赖子没有理会他,在他眼中郭辉和徐磊是一个人,是一个疯子。每天不断滚石头上山的疯子。从疑问,反对再到暴跳,愤怒,大叫,跺脚......可都已经没用。他的反应或许是太激烈了些,在有人支招,安抚后才渐渐平静下来。
移村的工程马上就开始实施了,河城的东西很少,从架起木头到抬完最后一个箱子,只用了一周不到的时间。唯一没有拆除和搬动的就是那座孑的祠堂。它还在那里,它是村里人的信仰,但这玄乎的东西只有李家人懂,它是村里人建的没错,但出入的仅是李家人。
人们能看见天空了,也能看见海了,知道什么是滩涂——一脚踏进去准能让泥巴在你腿上刷一层漆。不再是在肆意生长的榕树统治下的,一个山头与另一个山头,没有烦人的苍耳和有半个人高的狗尾草。没有长达数月,让人想呕吐的脏雨。一切都似乎很美好,似乎也没有人接着思考和在在意土地分配的事儿了,有些处于想了也无可改变就将之抛掷于脑后了这个问题只要有一个或两个人思考着,就够了。
在移村搞得差不多后,人们也要开始适应新的一切了。屋顶不再是茅草而是棕榈叶,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捕猎的场所不再有拥有厚厚的皮毛的四脚动物,不用担心头顶有竹叶青。有人适应那也必有人不适,因而怀念过去,指责当下。抱怨和牢骚从未在新河城消失过。李赖子显然并没有打算接受移村的一切。当初他是如何的暴跳如雷,最终他还是跟来了。
说来奇怪,到了海边不应该是有狐狸叫的,人们晚上还是时不时听到了狐狸的叫声。像狗,但是声音更脆,音域也更小一些,更宛转动听。仔细听,又像是鸡鸭的叫声。时强时弱,夹杂在海浪的声音中。
反复几夜后,人们及时地开始讨论他们听到的。有人甚至模仿起了那种叫声,不要说,还真有几分像。
移村前后,徐磊和郭辉都在那边下棋,换了一个地儿,同样的桌子,同一副棋盘,同样缺了俩棋子。
“诶,老徐,你听到了吗?”
“嗨,这群人,又玩起了老把戏。”老徐的棋子往前挪了几步。老李没有剃胡子,显得有些苍老,他知道这局棋又是同样的结果,无论他怎么乱下子总能赢棋。
“诶,我又输给你了,大意了。”老郭用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后,老徐低头接着看着棋盘,下巴与脸部的皮肤挤出一道道深深的沟壑,形似老镇的山沟子。
狐狸叫从出现起再也没有断过,和当初在山里的如出一辙,一样的长而慢,一样的时强时弱。一样的宛转,相似美妙的乐手和人的歌喉。
移村之后,没建孑的供堂。人们很听话的建起了公堂,比上次的还要漂亮,还要精致,从木雕到石雕无一不精雕细琢,以祈求孑的声音。李赖子非常自然的入户了祠堂,以传达立孑的旨意,用不清不楚的语句表达着明明白白的意思,这个分地不合理不公平。
然而,他们还不属于这里,没有理由瓜分这里的山川万物,只要没有死人埋在这里,这个集体就不属于这个地方。
但确实,土地并没有重新分配,即使江渝请算数最厉害的专家,用最精密的仪器做标准的尺规作图,土地也无法做到完全平均,事实上从未有人想要平均分配,平均分配只不过是在自己得不到好处时的最坏打算罢了。
这种意图和诉求,藏在海腥味的风里,顺着海浪越推越大,一次拍打着江渝伟岸的肩膀。江渝只是沉默,他没有走出他精致的小屋,在布满图纸的老樟树桩子上画着一笔,两笔。
海浪一波弄一波,都显得有些躁动不安。海风无缘由的日益猛烈。
人们开始害怕。狐狸的声音总在夜间隐约的在梦的泡影中诉说着什么,有人觉得这个声音很美,美的让人陶醉,如果没有这种声音,就无法入睡。有人说这是孑的声音......
时间差不多了,一个声音出现在了本就有些聒噪的剧本里,使得有的人发觉过来,继而自觉聪明,不再前往孑的供堂,有些人依然保持这份习惯,但没有以前那么殷情了。
现在的河城依然保留着这座孑的供堂,前来观光瞻仰的人很多,排不完的长队前来祈福,买赎罪券。展厅边还有着保护文物,请勿触摸的警示牌。当然在这边上也立着江渝的像,刻着他的传说。
海水洗漱礁石声,风声,鸟叫声,再加上夜间的狐狸叫似乎一齐为一副不完整的剧本开始排演。雨也开始下了,打到井里,水渠中,海田里,滴滴答答,不那么清脆。
雨是脏的,将本来就不洁净的地方搅得更加邋遢,雨水黏着泥土跳进拖鞋里,钻进脚趾缝中。和当初山里一样,雨并没有变得干净,它总将世界搅得胡乱。
天色渐深,雨渐渐停了,滩涂边,河城人开始抓青蟹,小镇里能听见噼里啪啦干柴燃烧的声音。
那是一个晚上,江渝喝醉了,大喊“狐狸,你别叫了,我知道你在听。”他拿着酒瓶,踉踉跄跄的回了屋子,人们躲在窗后,探出一条缝儿,看着他跌跌撞撞的影子。那夜,屋子里的灯没熄。
晨光开始吸收回黑夜赠予的露水,那间漂亮的房子里出来一个小孩,一丝不挂,很干净,像刚消融的冰一样干净,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告诉别人,他是江渝。
笑的很灿烂,他没有穿着笨重的鞋子,累赘的衣服,光着身子迎着海风跑,海风都变得甘澈了,踮过滩涂,越过沙滩,跨过海边长满牡蛎的岩石.......他跑的很快,孩童似的没有变声的嗓音常常传回河城,那是最天然的笑。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关心这个,为塑造他走的合理性,人们虚构起一宗宗罪状,但他不会回复。他的房子是河城最漂亮的,是离淡水井最近的,人们知道他是天生的领袖,他提议走出的山林,他提议挖起的井,他教会人们如何利用海塘,如何如播种般饲养鱼苗,怎么挑时间和地方抓青蟹,他好奇于技术,他利用藤蔓和木板创造了早期的轮滑和杠杆。他提议家家户户前都要通水渠,一户人家与一户人家间的路要宽要大.......
他去往的地方应该很亮吧,是刺眼的黑,还是暗淡的白。
确实,一切都很合理。
没有人再去开拓土地,逼得每个人都得往外探索。现在河城的格局和轮廓也从那时慢慢画定。
李赖子显然不可能得到他所期望的,事实上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土地。
他向人们诉说着这不合理,挨家挨户的。只有心肠软的老人还附和着他。
没见过海的人怎会模仿海边的声音呢,人们在夜里还能听见狐狸的叫声,和叫声中新的诉求,可那已变成了笑话,成为谈资,沦为每晚的娱乐和配乐。
“小子,过来学下棋吧。”
李赖子好像疯了,他们是这么说的,是河城里除了李赖子的所有人是这么说的。是他蓬乱的外表,干裂磨损破碎的指甲指着每一个人。黄昏下,落幕的戏剧里,还有一个没有卸妆的演员。
“那小子还是没变,怎么叫他学下棋都不学。”
说着,郭辉的車又吃了徐磊的馬。
夕阳躲回了海洋的庇护所,映染了半片天空。两个老人在红色的画布下涂鸦上举棋落子的阴影。
几天后,
有人发现——
李赖子死了。狐狸也再也没叫过。河城有了第一块墓碑。
2020.12.18
《八尾狐图》,1637,德川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