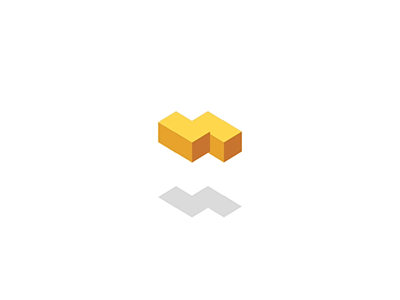大约公元前2000年,最初说印欧语的半游牧原始人被一些自然灾难(可能是干旱、长期的冰冻或饥荒)驱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最有可能生活在里海( Caspian)与黑海( Black sea)之间的地区。无论他们分散的原因何在一一甚至可能是由于中亚的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一一古意大利人的、希腊人的、德国人的、英国人的、凯尔特族的( Celtic)、伊朗人的、说梵语的和现代说印地语人的祖先为了生存下来,被迫从俄罗斯南部逃离。这些部落四散开来,分成更小、更有凝聚力的单位,赶着他们成群的牛、绵羊、山羊和驯养的马,在欧洲和印度的历史上翻开新的一章。赫梯人( Hittites)是定居在新家的第一批印欧人,因为我们仅在卡帕多细亚( Cappadocia)的高加索( Caucasia)南部发现他们的踪迹,确定其时期大约为公元前2000年。不过,其他部落继续向前走;有一些越过安纳托利亚( Anatolia)向西,另一些越过波斯(现在被称为伊朗,雅利安人的亲族,因为印度一伊朗语是由印欧人在公元前1800至前1500年间被带到这一地区的)向东。印度一伊朗人(IndoIranians)似乎在他们长期移民之后曾经和谐地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不过,到大约公元前1500年,他们好像再次分裂,历史上所说的印度一雅利安人(Indo- Aryans)游牧部落,或简单地说雅利安人继续向东前进,越过危险的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
 ...
...
印度关于语言祖先的最早历史的知识来自像弗里德里希·麦克思・缪勒( 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这样的语言学家,他们在一个多世纪中耐心重建移居史,并发展了语言古生物科学。通过对这一语言大家族中所有语言的分析和对地理、气候、植物、动物共同术语的抽取,尽可能地绘出了“最初家乡”的生态图,它与高加索的极其相像。激发了比较语言学和语文学的出色的、具有独创性且卓有成效的见解是由威廉・琼斯( William Jones,1746-1794)爵士公布出来的,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高级法院( High Court)的法官。威廉爵士在他1783年到达加尔各答后开始学习梵文,三年后他撰写了一篇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其中提到了使印欧语系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梵语都具有亲缘关系的词汇和其他语言要素。
 ...
...
我们并不拥有印度雅利安时代(约公元前1500一前1000)第一世纪的任何考古证据,但我们能够从雅利安人的宗教“知识圣典”或吠陀( Vedas)中拼合出这一时代的图像,吠陀是由每一部落的游吟诗人通过严谨的口头传说勤勉地保存下来的。这些圣典中最古老、最重要的部是《梨俱吠陀( Rig Veda,字面意思是“知识颂”)》,由1028句梵语偈颂构成,其中大多数是献给各位雅利安神并请求得到他们的恩惠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印-欧文学遗存。
 ...
...
与哈拉帕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人们不同,雅利安人与他们迁移来的牧群一起生活在部落村庄里。他们的房屋用竹子或轻木料建成,经受不了时间的侵蚀;他们并不烧制砖,没有建精致的浴室或下水道,没有雕刻华贵的甚至朴素的塑像;他们没有印章或着作,没有彩陶工艺,没有极好的房屋。这些相对原始的部落人群难道竟能够强攻和征服构筑堡垒的印度河城市?也许。他们把马套上战车,而且他们似乎挥动着带柄的青铜战斧(在印度河域市的最上层曾有发现),还使用长长的弓与箭。经过集体迁徙他们变得坚强,忍受了使手脚起水疱的毒阳光,并翻越了冻雨和雪密布的高高的关口。不过《梨俱吠陀》对这种旅程以及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没有反映,它确实提到雅利安人夺取了“构筑堡垒的地方(pur)",黑皮肤的人们(达萨人)在他们的堡垒中试图徒劳地防御肤色更白(“小麦肤色”)的雅利安人。(梵文词dasa后来逐渐有了“奴隶”的意思。)
由于《梨俱吠陀》在约公元前600年之前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并且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本只是在约公元后1200年,首先我们会问:当像一般假设的那样,雅利安人首次侵入印度之时,我们如何知道早在公元前1500年吠陀颂诗真实的创作情况?在1909年之前,麦克斯・缪勒的“回溯推测( dead-reckoning- backwards)”的技巧是粗略估计吠陀年代的唯一方法。麦克斯・缪勒从语言和观念的角度对吠陀文献的整个本集进行分析,他注意到梵语在示格词尾、词形、句法、词汇和意义的各种变化。他确定了在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用多长时间产生同样的变化并形成了梵语演化的类似时间表。那些依然被印度教徒视为“启示”或天启( shruti,字面意思是“听闻的”)的吠陀圣典的演化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梨俱吠陀》和其他三个古老颂诗、符咒或咒语的“本集( Samhitas)”:《娑摩吠陀( Sama Vedas)》、《夜柔吠陀( Yajur Vedas)》和《阿闼婆吠陀( Atharva Vedas)》,它们均为古老的诗体文献。接下来产生了一系列对每个吠陀进行注释的散体文献,对那些通常意义含糊的颂诗进行详尽阐述,并且细致地描述准备吠陀祭祀和恰当地抚慰诸神要求的具体步骤。因为它们提高了雅利安祭司阶层婆罗门( brahmans,源于“神圣的言说”或“那些唱颂神圣言辞之人”一词)的作用和意义,所以那些注疏被称为婆罗门书( Brahmanas,或梵书,净行书)。
最后产生了第三组神秘哲学着作,其主要形式是诗体对话,而且其激进的新宗教信息将其自身与婆罗门书和本集之类彻底区分开来;这就是吠檀多的《奥义书( VedantaUpanishads)》,其中的许多观念与早期佛教的类似。缪勒推断它们定创作于大约佛陀生活的时代,或大约公元前6世纪。不过通过回溯推测法,他估计留下的108个奥义书文献也许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这期间即使没有语言上的变化,观念上却有比较大的改变。这将使其创作时间向前推至约公元前8世纪,其后至少两个世纪才编写了梵书。如果吠陀本集的最后一批在那时已经完成并且为公元前1000年的注疏做好准备的话,那么《梨俱吠陀》最古老部分至少要早于它四个世纪,作出这样的推断似乎是安全的,因而《梨俱吠陀》的编写时间被确定为大约公元前14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