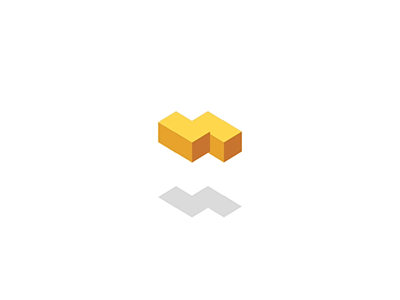...
...
飘香的菜园
姐姐大学毕业后,去了南方一座城市工作。我也参加工作成了家,并在镇子里买了房子,离开了父母搬出去住,父母依旧细心照料着家中的那片菜园。
新买的房子较小,院子即是园子,坐落于主街旁一条巷子的最深处,紧临镇中学西墙。墙东是学校的几排柳树,柳树那边是开阔的操场和新建的教学楼,由于教学楼距离这边较远,学生很少过来吵闹,我倒是很惬意这份相顾相安的静谧。
搬家到镇里那天,正是植树节,一周之后便是春分。可东北的春分时节不见春,甚至在春分后还落下了几场雪。但与千篇一律的春天相比,也好,独立园中,且趁无花赏雪花,这样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美呢?
门前的巷路通到我家,也便到了尽头,有的学生便攀越门前的墙头抄近路,来回于家和学校之间。久而久之,墙垛上有的横砖便被蹬掉了,有了豁口后,上上下下跐起来方便多了,我也偶尔翻过墙头到宽绰的操场上活动活动筋骨,压压腿,散散步。一天,在只有一墙之隔的操场边缘,突然发现了几丛迎雪而开的黄色小花,后来才知道,这种花叫连翘花。这里的人常常称春天里最先开放的这种小花为迎春花,其实这是不对的,迎春花是六瓣的,而连翘花则是四瓣的。对于这种凌寒而放的小花我情有独钟,敬佩有加。只可惜当时还没有学写诗词,否则是否也会像今天一样吟出“新芽势可期,唯恐报春迟。雪去添金色,花开第一枝”这样的诗句呢?
 ...
...
赏过红墙外雪韵中的连翘花,差点错看小园偏僻墙根处一簇不起眼的灌木丛,直到芽苞抱满枝头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它将是小园早春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无数的蓓蕾蘸着和煦的阳光,没过多久,便将满树绽放得花团锦簇,馥郁芬芳。这树花先开花后长叶,叶子好像榆树叶,花朵酷似梅花,因此叫榆叶梅,又名小桃红。有了这一树怒放的花朵,真可谓“枝头春意闹”,整个小园也萌动起来。
窗前的砖缝里,朝阳的垄台上,嫩嫩的小草萌发新绿,蠢蠢欲动。我在小园中撒上土粪,笔直地打好垄,陆续栽种上各种蔬菜,仔细打理着。小园中的绿色日益生长,不断膨涨。
在墙角,我用松木杆和杨木方搭起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大木架,靠近木架下的两条对应的边线种上丝瓜、冬瓜、砍瓜等各种爬蔓的瓜。据说砍瓜的果实特别有趣,可随吃随砍,且可再生。小苗出土后,沐浴着春光,扭动着腰肢,吸吮着大地的养分,伸展的枝蔓不断噌噌向远爬。我挨着苗根在木架下斜支了一些木方,并用撕好的小布条小心翼翼地捆扎好翠嫩的枝蔓,将它们向上引。两面分别铺开的绿色不断攀高,就像要比出个输赢一样交错纵横爬上木架,在枝繁叶茂间开花、座果。溽热时节,我常常在浓阴匝地、风清气爽的木架下,慵懒地靠着木椅,对着摆放了一盏茶、一卷书、一把扇的木桌,透过斑驳的光影,仰望着葱葱茏茏、遮天蔽日的绿叶,和垂在藤藤蔓蔓间形状各异的瓜,暑日里内心的聒噪早已被这欲滴的翠色荡涤得云淡风轻了,周身上下只剩下一份悠然。
 ...
...
室内的花架上和书案旁摆了几盆文竹、绿萝等观叶绿植,室外的窗台上、井台上和过道旁,错落摆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花盆,栽有木槿、常春藤等二三十种花花草草。随着所物色来的花的品种不断增多,现有的花盆已显不足,我便将花直接栽在地上。就这样,小园除了是我的菜地,还是自然的舞台,荡漾在微风中的花儿次第开放,虽无姚黄魏紫,但得怡姿雅韵,疏密有致的花朵周遭蜂来蝶往,墙外柳影婆娑的枝头鸟鸣啁啁啾啾。时常有鸟儿灵巧地站立在房檐边或晾衣绳上,啄啄羽毛,机警地四处张望,突然发现我悄悄地就站在一旁仰头看着它时,便倏地展翅飞走。对于我来说,这样反倒愈增加了几分悠静。
花儿和蔬菜越长越高,莳弄起来需要来回过往穿梭,很不方便,我便在墙边和菜园中间铺出两条红砖过道。每天一大清早我便起床,到户外踱步于花草果蔬之间,摘菜薅草,赏花拍照,徜徉于小园香径之中,呼吸着溢满清鲜的空气。在悠哉悠哉,颇得乐趣之后,才吃早饭,去上班。夜晚,静静地躺在土炕上,花草的芬芳飘过窗子,随着鼻息与我的梦香交融在一起,蛐蛐儿声和各种虫鸣的夜曲在梦的深处欢乐地打着滚,一夜的酣眠足以消退万分的疲惫。
 ...
...
斜挺的竹竿架却甘愿背负着一种名叫“压趴架”的豆角,六月繁茂的架上绽放出无数淡紫色的小花,凋落后细密的豆荚挂满枝头,直至豆荚又宽又长,豆粒又圆又大。一次只需摘十几个,配以土豆,便可以做出足够两三个人一顿饭所享用的美味——豆角炖土豆。再去菜地里随手摘来顶花带刺的黄瓜、脆生生的尖椒和嫩绿的小葱,只需用清凉的井水轻轻冲洗一下,便可以蘸着酱缸里酿出来的香浓大酱,再摆上一盘红白相间的糖拌柿子,就可以简简单单美美地大餐一顿了。邻居大姐看着我家架上的豆角招人喜爱,不禁啧啧称叹,我便给她和周围的邻居摘了一些,她们吃后也觉得味道甚美,我也很乐于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情怀,常常摘给她们豆角或让她们自己来摘。架上的花落了一层又开一层,豆角摘了一茬又长一茬,直至秋天,还是剩下一些未及宠爱的豆荚,干巴巴地凋零在架上了。
秋阳拂面,金风振衣。天地间仿佛都笼罩上了一种单一的色彩,然而万物秋黄中却酝酿了一派收获丰盈。砍瓜、冬瓜等挂满了木架,有的甚至足有十多斤重,真叫人担心一阵风来,便会瓜熟蒂落,重重地摔落下来。有的藤蔓甚至爬到车库的房顶和隔壁的院子里。下霜前一天的午后,我跐着墙头,爬到车库顶上。呵!没想到略微倾斜的几平方米的石棉瓦片上,竟然偷偷生长了姿态各异的十几个冬瓜、砍瓜、倭瓜,和园中的瓜儿一起采摘下来,竟有几十个之多。我将它们放在菜窖中储备起来,留着慢慢享用。
数九隆冬,白茫茫的小镇在厚厚的积雪中矮了一截。小屋内,红通通的柴火在灶膛和火炉中噼噼啪啪打着节拍,跳动着欢快的舞蹈,燃烧着粗犷的激情。此刻,从初秋松软的垄上刨出来的圆滚滚、胖乎乎的土豆、地瓜,和一大搪瓷缸的辣椒酱,正卧在大铁锅里咕咕嘟嘟乐开了花。热炕头的饭桌上,摆着一碟刚刚炒好的花生米和几个农家小菜,正期待着一场围桌热语。
好友与我兴致勃勃地坐在暖烘烘的火炉边谈笑风生。窗外,那片昔日溢满生机的菜地,正裹着厚厚的雪花被为终将醒来的春天而酣然入睡。天空中扬扬洒洒的薄雪恰似玉女摇落的梨花,在天地之旅间步履歪歪斜斜,就像醉入了飘逸到户外的红炉煮酒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