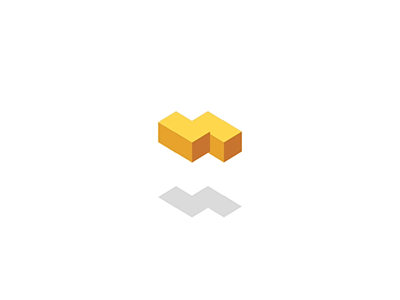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超越中国的贾玲,成为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
这一成就当然直接归功于《芭比》。
《芭比》上映后,鲜明的立场、尖锐的话题、连续的金句输出,还有鲜艳浓烈的粉嫩风格,一系列操作让此片在全球掀起了一场粉红热潮的海啸,且该片的票房大有可能会超越目前的全球年度票房冠军《超级马里奥》。
对格蕾塔而言,《芭比》并不是她最优秀的作品。导演生涯的首秀作品《伯德小姐》,以及翻拍自经典文学作品的《小妇人》(2020),更能体现格蕾塔的文学功底和对现实议题思考的深入。前两者的积淀,可以视为此次粉红狂潮积蓄的力量。
但短短三年内,“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的位置,先后更换了两位风格迥异的女导演。这一现象无法被我们所忽视。
将贾玲与格蕾塔放在一起直接对比,或许有点不恰当和不严谨。贾玲和格蕾塔,二人的优势专长、个人表达和职业目标都各有千秋,正如“芭比”和“李焕英”之间的强烈迥异。
但正是因为“女性导演”在全球电影工业的稀缺性,还有两人先后登顶“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的成就,又让她们在某些层面上自然而然地被放在一起讨论。
毋庸置疑,《芭比》与《你好!李焕英》(简称《李焕英》,下同)有着一份明显的共同点:即皆属于类型鲜明的商业片,话题性浓度大于思考挖掘深度。
《你好,李焕英》剧照
但《芭比》依然是一个相对保守、安全的,中产主义的女性叙事。影片最后将对主人公的拯救交给代表资本的美泰公司,更是引来不少不满嘘声。只不过大多都被呼声掩盖了。
说得更直白一些,《芭比》与《李焕英》的意识立场与价值取向都清晰强烈,二者各自属于两种不同层面的“政治正确”。
当然,两者还都讲好了一个故事。这是电影工业里一切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同样的故事,交给男性导演和交给女性导演去拍,也许会让观众看到完全不同的影片。这能解释为何近年来对女性影片、女性导演的讨论不绝于耳。
人类的故事有着不计其数的排列组合与讲述方式,有时候,在技巧之外,真正暴露个人表达的是一个镜头的呈现方式,一句台词的表达语气,一处闲笔的处理习惯。
芭比和李焕英
2021年初《李焕英》在中国的爆火,原因是多面的。一个以传统情感为内核的商业叙事,最终能拿下超过54亿人民币的惊人票房,靠的更多不是艺术技巧,而是由歌颂母爱所激发的观众眼泪。
导演贾玲第一次拍电影,动因很单纯,大概率不是奔着“票房第一”去,而是为交代个人情感。
《你好,李焕英》剧照
在当下由受众投票的文艺市场,你永远不知道哪块蛋糕被观众选中,而复制增产的下一块会不会被买账。
《李焕英》上映后超出所有人预料的市场表现,似乎暗示着一种契合时代潮流的风向:女性叙事在今天,是可以拿来冲“票房第一”的。
但即便欢呼沸腾也没法否认:《李焕英》当然不是女性主义电影,它只是“与女性有关”的电影,是一部由女性导演拍摄、以女性为主人公、探索女人之间关系的影片。
此片上映当年,笔者采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影评人毛尖老师,后者直言评价道:“《李焕英》里的母亲和20世纪80年代的《妈妈再爱我一次》里的母亲,并没有本质区别。”
“李焕英”延续的是中式家庭框架内的传统女性形象——母亲,无私奉献的母亲,隐匿自我的母亲。她能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原本存在的、最原始的,对于母亲的依赖和歌颂。这无可厚非。
年轻的母亲李焕英(张小斐 饰)
但在今天,女性主义叙事仍是多少带点先锋性和后现代性的东西。因此,我们对女性叙事的期待,是能提出具有质疑性和挑战性的思考,也会与现实生活形成互文关系。在那个虚拟的镜像和文本里,“她们”能为现实中的“我们”找到某些出路与可能。
同样作为现象级影片的《芭比》,其爆火更多是事先张扬。至少,从话题与类型来说,能在中国大陆见到一部不加掩饰的、亮出女性主义旗帜的商业片,是比较少见的。
如果要论其有何“先锋性”,首先便是“真人芭比”这一基础设定。兼具科幻性与喜剧性,将对意识的讨论贯彻到了一个被商业资本塑造的非生命实体身上,这本身就包含电影所需要的意外和超前性。
然后才是从罗比饰演的主角“芭比”角度出发的,影片直白强调的“走到真实世界”。将“完美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对比作为女性觉醒的支点,企图消解性别符号的象征和绑架。
《芭比》剧照
不过,从头至尾,芭比经历的世界都是“奇遇”型的。她没有解释,为何会在现实社会经历各种被冒犯行为?也没有对此进行深度反思,甚至到最后,探索与反思在愉快的氛围里终止,依旧落到了一个标准好莱坞式的“爱与和平”结局。
在西方审美体系里,这是中产的保守主义。在中国哲学里,这是浅尝辄止的、和稀泥的中庸。
格蕾塔自己曾在采访里阐述:《芭比》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电影之旅。它的确既像乌托邦,也像短暂旅游,“芭比与肯”们生活在一个悬浮的虚空世界,不会生老病死,没有生殖器官,没有真正的武器,个人其实并不从事真正的劳动活动,而只需要进行角色扮演……
在这种感受不到疼痛与情欲,隔绝生死与疾病的世界里,讨论女性的“觉醒”,就像讨论哪个芭比娃娃该定价高一些一样,仿佛一场巨大的隐喻和谎言,徒浮表面。
《芭比》剧照
而另一位“最高成就女性导演”贾玲,她镜头下的母亲感人至深,温柔慈祥,是我们每个人渴望的母亲,也可以与大多数观众的生命记忆产生联结。这是情感的巩固,而不是挑战,是可以放松背靠后倒下的柔软海绵,而不是坚硬的跑道。
北京大学教授、学者戴锦华曾说:女性电影的意义在于,我们期待“她”能够建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能够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去拓展我们的世界。
对传统没有挑战,或是挑战不足,都足以被视为“虚假的女性主义”。反思和挑战传统,并不一定是为了打破或扭转它(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为了创造出某些有别于当下的正面的变奏。
而对于格蕾塔,戴锦华也有着另一句评价:“(她是)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一种文化象征,一种趋势性的代表人物。”
被异化的格蕾塔
在“全球票房冠军”这个名衔之前,格蕾塔已经在影坛熠熠闪光一些年头了。
这位出生于1983年的青年导演,早在2012年就有一部编剧并主演的《弗兰西斯·哈》(Frances Ha)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短名单;2017年,凭着《伯德小姐》(Lady Bird)一作,格蕾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成为奥斯卡史上第五位获得该提名的女性电影人。
《伯德小姐》是迄今为止“格蕾塔色彩”较为浓厚的影片。
在这部典型的布鲁克林文艺青年叙事里,女主角克里斯腾是个特立独行,强硬叛逆的中学生。与《芭比》里展现的一样,克里斯腾也处于一段僵硬的母女关系之中,常与母亲因价值碰撞产生冲突和矛盾,也不满被传统的家庭方式束缚。对自身前途与命运的迷茫,迫使克里斯腾回望自己的欲望和成长。
《伯德小姐》剧照
从“伯德”到“芭比”,其实已足以看出,母女关系是格蕾塔擅长的,甚至是有所执念的一个重要叙事支点。如果深入挖掘这一女性题材里相对稀缺的关系题材,她一定能给出足够深刻和细腻的出色表达。
不过,迄今为止,这一可发挥空间巨大的女性关系,在格蕾塔的叙事里尚未真正成立,她大概还没有将女性个体生命成长的探索,熟练地转换到代际关系里进行剖解和延展。
完成、回归女性的主体性,仍然是格蕾塔现阶段最主要的画布。《伯德小姐》之后,她执导了直接由文学文本改编的《小妇人》。从小熟读多遍原著的格蕾塔,拍出了史上第一版最终凭借努力获得个人职业成功的女主人公“乔”。
《小妇人》剧照
格蕾塔还在电影里巧借角色之口,说出了原作者另一本小说《Rose in Bloom》里的句子:“女人也有头脑也有灵魂,不是只讲情感,女人也有雄心也有才华,不是只有美貌。我很讨厌人们说女人只能为爱而生……我烦透了。”
女性意识并非在此刻萌发,而是经历“伯德小姐”的成长和探索后,变得更铿锵,更有底气地落地。
或多或少能从创作中看见自己前半生的影子,这也许是女性表达者较为鲜明的一个特点,且不仅仅限于电影表达上。
格蕾塔出生于1983年的加利福尼亚州,从小喜爱看戏和演出,曾梦想长大后做演员。“我认为自己之所以享受做电影人而不是写学术论文,是因为(做电影)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得到不同的想法,不必落在一个答案上。”
格蕾塔·葛韦格
但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十九岁那年,格蕾塔考入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女子文理学院巴纳德学院,学的却是学英语和哲学。她疯狂尝试各种表演活动,成立过即兴表演小组,还申请过几个剧作家艺术硕士,却皆被拒绝。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做到。我继续创作,但嘴上却一直推辞,因为我感觉这不是我能做的事情。”
直到遇见兴起于00年前后的美国独立电影运动呢喃核(Mumblecore),格蕾塔终于等来了适合自己发挥的空间。
该运动以非专业演员、低成本、自然主义即兴表演的影片为主,故事主体集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关切他们的生活状态、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呢喃”,一种细碎的、渐进的、没有明确目的的低语,它并不致力于达成什么结论,而是集中注意力关切生命本身的状态。
像格蕾塔这样的,更注重个人表达而非工业呈现的导演,该运动仿佛就是为她而生。
电影史上不乏关切女性生存状态的男性导演,包括不少行业顶级大咖比如岩井俊二的《花与爱丽丝》,雷德利·斯科特的《末路狂花》,讲述卫生巾发展史的印度电影《印度合伙人》等等。
雷德利·斯科特和岩井俊二
但在女性导演镜头下,女性主体细致而微的感受通常会被赋予更多笔墨,这也是格蕾塔最初脱颖而出的优势所在。
从小成本独立影片起家,最擅长向内刻画女性细腻的内心情感,总是能作为一个诚实、敏锐的表达者,释放出一些独特的惊喜。
因此,在“去人性化”的芭比身上,格蕾塔这份才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虽然类型化鲜明,视觉冲击力更强,但过于“安全”“标准”的《芭比》总是给人一种感觉:此“格蕾塔”非彼“格蕾塔”。
女性主义的“蓝海”
当我们从“杨紫琼”谈到“格蕾塔”,盛赞各种“女性力量”与“女性声音”,现实似乎在创造更多希望和可能性:人们将她们归纳为某种反传统格局的佼佼者、集万千女性歆慕目光为一体的“楷模”,关注她们如何冲出重围,克服万难,走到一个常年由他者占据的荣耀之位。
然后,聚光灯重新回到她们最负盛名的“成就”之上——即关于“女性”的内容表达。
从这个层面看,“女性主义”,同样被迫成为了这些女性创作者的“工具”。她们被世界看见,是因为她们用女性身份去表达女性故事,完成了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可以被高度市场化的符号表达。
怎么想,都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
再看看《芭比》吧。片中坦然裸露出来,却并未试图做出解释的一个设定,就是女性的“被商品化”。
请注意,“商品化”和“物化”是有区别的,就像芭比可以同时被推到舞台中心,接受闪光灯的簇拥,受人欢呼与呵护,也可以同时被标件生产及售卖。消费者可以真诚赞美她完美的胸部,精心保养她高质量且环保的躯壳材料,人们标价她的同时赞美她,利用她的同时也哄骗她。
《芭比》剧照
对她真正产生恨意的,只有成长于“Z世代”的,作为“半成品女人”的小女孩。因为后者知道“完美”的陷阱,瞧不起她努力让自己变成消费“标件”的自我麻痹心态。
这种消费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正是“商品化”的结果。因此,哪怕大张旗鼓打出“看见女性”的旗帜,就算叙事稀烂,也可以靠响亮的口号、浮于表面但取材生活的套路故事,赚得盆满钵满,收获护卫军成吨。
比如看似呈现“女性友谊”,实则利用大众“渣男创伤”巧弄叙事的《消失的她》。其误导性和沉沦性,比作为情感按摩椅的《李焕英》恶劣多了。
《消失的她》剧照
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更不是我们应该在大银幕上看见的女性电影。女性相关话题可以提炼出来的情绪糖果可太多了,从祖辈的封建压迫,到家庭层面的性与暴力、社会层面的歧视与偏见……随便挑一样,不管男导演女导演去创作,都是一片安全的大好蓝海。
是利用“女性主义”炒热文艺市场,还是为了社会进步而重视并改造现状,二者或许有一个隐性的标准——即是否真的有人愿意花心思坐下来,聆听一个并不中心、并不“昂贵”的女人的心声。
这也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精彩与宝贵之处。她和“正常的”格蕾塔一样,并不执着于从“结构化”角度探讨女性的处境,不用自怜和愤怒的姿态批判婚姻和现实的荒谬,而是向内回到女性个体的心灵成长与隐微痛楚,尊重她们原本的声音,重新定义那些曾经被贬为“歇斯底里”的痛苦和欲望。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我的天才女友》在情节上没什么超凡脱俗的,但那些历来被粗暴概括的、被压制于符号与规训之中的个人,在作者剖心般细腻的刻画下,前所未有地活了起来。
票房冠军,一生得一次足矣,至少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部“格蕾塔”,或许没了华纳与美泰的重金支持,但应该也不必这么别扭尴尬地呈现“女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