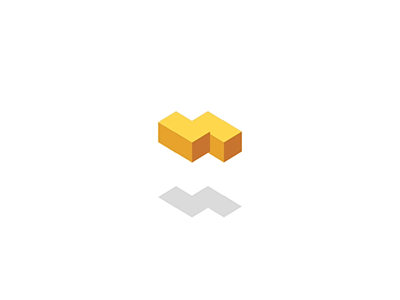...
...
明清时期的城市中,书籍在私人藏书楼中存放,在坊间书肆中流通。清末民初,江浙地区的地方精英与清廷合作,逐步开始创建讲求“公共性”的新式藏书机构。民国时期各种公共图书馆先后创建。伴随新式出版业的发展,图书馆、书店与书摊,是现代城市中书籍存放与销售流通的主要场所。作为现代城市文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空间,图书馆负载着对公众进行知识普及与文化教育的作用。书店与书摊,则是遵循市场规律运作的出版业最主要的图书销售终端。这几个与书籍有着密切关联的城市空间,是知识群体文化生活最重要的几个空间。
图书馆——知识群体的公共阅读空间
民国以来,为普及教育,除加强学校教育外,还特别重视社会教育,故各种通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教育馆等社教设施纷纷成立,数量日增。馆藏的内容,亦由深奥趋于实用,尤其是五四运动及平民教育运动以后,收藏的图书种类不再限于珍本、秘本、孤本、钞本等,而渐以一般读者的需要为主,讲究实用性。时为学生或低级职员的青年知识群体,由于经济条件低下,难以拥有私人藏书,更不敢奢望有自己的书房,故图书馆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公共阅读空间。近代上海都市人口的剧增引发了巨大的阅读需求。与出版业蒸蒸日上的发展相呼应,政府也在公共文化设施方面有所作为。清末民初,就已有上海平民书报社、通俗宣讲社附设图书馆、江苏省教育会附设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南洋公学图书馆等各种私立图书馆及藏书楼。较具规模的如南洋公学图书馆,“前临操场,其建筑分四层……校外人惟星期六星期日可入阅,余供本校师生参考之用,来宾有介绍者得入内参观”。1934年出版的《上海导游》列举了上海市内的各主要图书馆:上海市商会图书馆、天主堂图书馆、江海关图书馆、地质研究所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社会科学研究图书馆、明复图书馆、工部局洋文图书馆、科学社图书馆、市图书馆。
17~18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一种要建设吞揽一切图书的图书馆的乌托邦计划。这类包罗一切人类迄今所写就文献的图书馆、百科全书和大字典,是启蒙时代的几项最重要的文化事业。而将所有图书都包含在一个图书馆的企图,暴露了现代性初期的文人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个内在张力:能够包罗所有图书的普世图书馆只可能是非物质性的,如目录,而作为物质性存在的图书馆则是有限的,只能包括已知知识总体的局部。这种张力从一个侧面也体现着现代性计划的总体张力。商务印书馆下属的东方图书馆因其规模宏大的图书收藏与系列文库和教科书的出版,不仅承担着上海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之职,还颇类启蒙时代欧洲图书馆的现代性总揽方案。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该图书馆有深刻的记忆。据董涤尘回忆,图书馆在编译所最高一层,“所藏图书相当完备,供编译所备用的古今中外各种参考用书,已相当丰富,凡中外包括西文日文最新出版的书,往往能及早购进”。“除善本另有手续外,是予取予求没有限制的。”沈百英甚至认为“图书馆藏书丰富,要什么有什么”。胡愈之认为自己一生中“读书主要是在商务读的”。
商务印书馆下属的东方图书馆
然而,近代上海的其他各级图书馆建馆之初就没有如此的雄心壮志。这些图书馆藏书情况各有不同,知识分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有些图书馆尽管藏书较少,但却给知识分子带来闲聊的意外收获。唐弢回忆了自己穿梭于几个图书馆之间的情形:
邮局的工作时间短,又比较集中,我利用这个便利,经常跑图书馆。邮政工会在福生路(武进路的支路)办了一个,藏书本来不多,大革命失败,稍有意义的都被清理掉了。附近宝山路上,却有个藏书丰富、全国闻名的大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离我住处更近,还有河南路桥的市商会图书馆。我消磨于这三个图书馆的时间,比到邮局上班还要多。从《国粹丛书》到《南社丛刻》,东方图书馆都有全套,但借书手续麻烦,最方便的是工会图书馆,却又借不到什么。借不到就闲聊。它给我的唯一好处是:我从借书人口中,听到了许多邮政工人在三次武装起义中的故事……要弄到一本好书很费事,图书馆里进步书借不到。
此外,上海一些颇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也成为知识分子时常光顾之地。始建于1986年的上海南洋中学,其图书馆藏书源于校长王培孙先生的私人藏书。在清末民初时,南洋中学图书馆内藏有王氏先人所藏多种古籍与哲学、历史、政典、方志、文学、笔记及珍贵的藏本佛经等约4000种图书。图书馆甚至还藏有一部分西文图书,分设中文阅览室和西文阅览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图书馆经过改造与扩建,其藏书量不断增加。黄炎培就曾多次去该馆翻阅图书。1928年4月底至5月初,黄炎培就频繁去该馆翻阅有关边疆与地方志方面的图书:
晨,至南洋中学,访培荪、天放,参观图书馆。
至南洋中学图书馆阅书,饭于培孙、天放所。
至南洋中学阅书。
在南洋中学阅书提要:《中山沿革志》、《使琉球实录》。
至南洋中学阅书:《中山传记录》、《读史方舆纪要》、《平定台湾纪略》。
然而,上海的图书馆毕竟良莠不齐。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条件优越,“馆内的桌椅,都是极漂亮的木料做的,馆内的工程书籍当然很多,线装珍本与英美小书也是应有尽有”。而一些私立大学因办学条件过于简陋,给知识分子带来极大不便。1927年,萧公权留美归来,居沪六个月。其间经介绍,先后在被他视为“野鸡大学”的私立南方大学与国民大学任教。由于学校没有图书馆,他对这段任教经历颇有抱怨:“我知道在这样的学校里任教,不是长久之计。学校没有图书馆,使我陷入无书可读的苦境。我由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书只能作‘温故知新’之助,不是取之不尽的学问渊薮。同事当中很少可与切磋的人,使我更有离群索居之感。”
一些怀有革命热情的左翼知识分子试图在小范围内创办私人图书馆。1930年代,同在银行系统任职的楼适夷与应修人就做了此尝试。
算盘、银元、钞票,使我们感到衷心的厌恶,周围唯有金钱能支配一切的处境,更使我们对人生怀着美梦的青年,发生呕吐似的感情。十几个在同样环境中受同样苦恼的青年,由贪婪的求知欲和服务文化的热情,大家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创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大家捐书捐钱,利用业余时间,把藏书无条件地出借。我们就是在这一工作中互相结合起来,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然后每人挟一大叠邮包,送到邮局里去寄给借书人……馆址也从铜臭的商业区搬到比较有文化气息的北四川路。工作广泛地发展开来,会员一下子增长到三四百人,藏书上升到上万册,经常有上千人的借读者。
图书馆也会偶尔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接头地点。1932年,金丁到上海后,通过赵铭彝找到周起应,赵铭彝“在四马路附近一间书局里做编辑,他为我和起应约好,准时在马斯南路的一个图书阅览室见面”。朱正明回忆自己加入左联时与组织谈话的情形,“当时左联另一位同志,约我在蚂蚁图书馆见面,我们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合坐在一条长凳上,秘密交谈一次”。
新旧之别——四马路的书店与城隍庙的书摊
而作为近代中国出版业与传媒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城市空间的变化体现在文化空间层面上即是,越来越多以售卖各种中西文新式出版物及二手书为主的书店集中在福州路与北四川路等新兴的城市繁华地带,而城隍庙一带则成为以售卖线装书、古籍为主的书铺与书摊的集中地。新兴书店与传统书铺及书摊三者并存,共同构成了上海最主要的文化空间。相较于旧书业,新书业由于具有资金周转快、利润高、更便于短线作业、面向顾客群体更大等特点,吸引了一大批怀揣各种目的的文人与商人投身其中。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
上海出版业的老前辈朱联保和包子衍在回忆中将1930年代福州路及北四川路一带的各个书店依次述及:
在福州路上,自东而西,店面朝南的,有黎明书局、北新书局、传薪书店、开明书店、新月书店、群众图书杂志公司、金屋书店、现代书局、光明书局、新中国书局、大东书局、大众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九州书局、新生命书局、徐胜记画片店、泰东书局、生活书店、中国图书杂志公司、世界书局、三一画片公司、儿童书局、受古书店、汉文渊书肆等;店面朝北的,有作者书社、光华书局、中学生书局、勤奋书局、四书局门市部、华通书局、寰球画片公司、美的书店、梁溪图书馆、陈正泰画片店、百新书店等,可见文化街上,书店确实是多的。在弄堂内、大楼内的,还不在内。在苏州河以北四川路一带,可说是第二条文化街,那地方除商务印书馆分馆外,有新知书店、群益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水沫书店、天马书店、春野书店、南强书店、大江书铺、湖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等十余家,而且都是在三十年代前后,出版进步书刊的。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分布在福州路与北四川路一带的新书店在密度与规模上都处于上海图书市场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北四川路文化街主要是因政治弱控而形成,福州路文化街的形成则缘于鳞次栉比的茶楼、酒肆、书场、妓院等娱乐场所的繁荣为书报业提供的无限商机。除此之外,在靶子路、虬江路还有不少以卖廉价中西文教科书及古旧书为主的旧书店。而文学史家阿英则详细描述了城隍庙一带以书铺、书摊为主构成的旧书市的情形:
你去逛逛城隍庙吧。……你可以走将出来,转到殿外的右手,翻一翻城隍庙唯一的把杂志书籍当报纸卖的“书摊”。……再通过迎着正殿戏台上的图书馆的下面,从右手的门走出去,你还会看到两个“门板书摊”。……在城隍庙正门外,靠小东门一头,还有一家旧书铺……如果时间还早,你有兴致,当然可以再到西门去看看那一带的旧书铺;但是我怕你办不到,经过二十几处的翻检,你的精神一定是很倦乏的了……
上海城隍庙一带的书铺与书摊,无论是其门面大小还是店面设施均既无法同开设在四马路等繁华路段的新式书店相比,也无法同江浙一带以售卖文房四宝及古籍善本为主的传统书市相比。为了维持售价的低廉,他们的营业场所不得不因陋就简,旧书店大多利用弄堂和屋脚铺起他们的店面;旧书摊大多在壁角和转弯处,放几个木板钉成的书架,插上旧书便算数了。
老上海城隍庙书摊
不但书店与书铺、书摊之间有新旧之隔,且在书店内部也有无形的等级之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店在给人以气势宏伟、琳琅满目之感的同时,也以其庞大的阵势与昂贵的价格构筑起门槛壁垒,让人望而生畏,无形中将那些文化场域中的弱势者拒之门外,以至于曹聚仁撰文指出,“商务、中华那几家大书店的势利眼,只重衣衫不重人”。在书籍的上架排列上,“把一切书籍高高地搁在架上,架前立着‘店员’,在店员之前又深沟高垒似的造了黑漆漆的高柜台,不用说买书的人不能够纵览书的内容,连小学生去买书也像进了裁判所一样”。
而一些中小规模的新书店则通过简洁朴实的店内装潢等给读者营造出一种亲近感。30年代中期,时为中学生的黄裳第一次在四马路买书时对于商务、中华等大牌书店“不无‘宫墙数仞’之感,只能怀着肃然的心情进去参观,那里的书许多看不懂, 更多的是买不起”。而位于宝山路宝山里的开明书店则让他眼前一亮,“店面里是一片明亮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新书多而印制精美, 绝无大书店出品那种老气横秋的面目”。
至于旧书店及书铺与书摊,其店面装潢较新书店简陋许多,图书的摆放也不像新书店那样整齐划一,往往任由顾客随意浏览翻阅,这反而令顾客感到轻松自在。开设在福州路的传薪书店,由于店老板徐绍樵大大咧咧的个性,书架上的书东倒西斜,长短不齐,台上、地板上乱七八糟都是书,甚至同一部书散乱放在几处,有别于新书店里井然有序的状态。然而正因如此,读者在这里可以随意挑书、乱翻乱扔,不受拘束,较为随便,尤其是一些年轻贫穷的读者,更愿意到传薪书店买书。有一些喜欢淘旧书的老顾客,一有工夫就溜达到传薪书店,甚至每天不去转一转,好像少了点什么一般。
因此,书店、书铺与书摊三者主要面向的顾客群体有所不同。分布在福州路与北四川路一带的中西文书店日渐成为出版业从业者、文学青年、大学教师等新型知识群体的光顾之地,而主要分布在城隍庙一带的书铺与书摊则成为作家、报人等具有传统文人特征的知识群体的淘宝之地。夏衍开始以翻译为职业之后,“就经常到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去买书”。由于日本的汉学医药书籍较多,以行医为职业的陈存仁“常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去买日本的汉医书”。鲁迅购买的各种外文图书很大一部分也由内山书店提供。1930年代在上海从事美术编辑工作的蔡若虹回忆道:“四马路的书店街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虹口的内山书店更是我们每星期必到之所,因为这个日本书店有许多介绍西方美术的图书画册,可以随便翻阅,不买也不要紧。”朱生豪在上海时,最常去的是四马路和北四川路上的书店。30年代的徐迟“到北新书店去买鲁迅,到现代书店去买戴望舒……外国书贵些,买外国书就上旧书店或旧书摊去买”。冯雪峰一到上海,就去逛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和在海宁路及吴淞路一带的日本旧书店;“望舒(戴望舒——引者注)到上海,就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施蛰存“到上海,先去看几家英文旧书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和别家书店”。
而如周越然、阿英、唐弢、郁达夫等带有传统文人特征的知识群体则热衷于光顾书铺、书摊及旧书店。唐弢“一有闲钱,也常常去逛书摊。城隍庙是每星期要去的”。除了四马路与城隍庙两个较大的图书市场外,三马路上也有不少旧书店与书铺。陈存仁“每天下午诊务完毕,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到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去搜购旧书,兴趣浓厚”。郁达夫更是对旧书情有独钟。陈翔鹤回忆起同郁达夫在一起的日子,“总爱一同跑旧书店,逛马路……而上旧书店的时候更特别多”。
“旧”的偏爱——知识群体认同感的建构
尽管许多知识分子既光顾新书店也光顾书铺与书摊,但四马路一带的新、旧书店与城隍庙一带的书铺、书摊两者主要顾客群体的不同,使得后者一方面被视为面向中低经济收入、在文化资本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知识群体的场所;另一方面被视为更具内涵与文化素养的饱学之士的乐园,具有那些位于四马路与南京路上的新书店无法替代的人生体味。左翼文学史家阿英对护龙桥、城隍庙一带的书市颇有好感:
这一带是最平民的了。他们一点也不像三四马路的有些旧书铺,注意你的衣冠是否齐楚,而且你只要腰里有一毛钱,就可以带三两本书回去,做一回“顾客”;不知道只晓得上海繁华的文人学士,也曾想到在这里有适应于穷小子的知识欲的书市否?无钱买书,而常常在书店里背手对着书籍封面神往,遭店伙计轻蔑的冷眼的青年们,需要看书么?若没有图书馆可去,或者需要最近出版的,就请多跑点路,在星期休假的时候,到这里来走走吧。
阿英这段带有个人倾向性的描述反映出他隐匿在文字背后的民众立场,也道出了城隍庙书市所面向的顾客群体有别于四马路的书店这一客观事实。而叶灵凤强调的则是对旧书店的偏爱。有别于新书店以销售新书与畅销书为主,旧书店及书铺、书摊上的书多是已经退出流行商品销售渠道的陈旧之书,这使得顾客在这些地方需要花费大量的闲暇时间,才能从中拣选出自己喜好的图书。在叶灵凤看来,逛旧书店具有新书店无法替代的功能和收获。
每一个爱书的人,总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因为在旧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时在新书店里错过了机会,或者因价钱太贵不曾买的新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好书,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着,一部你从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一部书存在的僻书……对于爱书家,旧书店的巡礼,不仅可以使你在消费上获得便宜,买到意外的好书,而且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验着人生,沉静得正如在你自己的书斋中一样。
购买旧书无疑在经济上更为划算。施蛰存坦言:“英美出版的新书价高,而卖英文书的旧书店多,故我买的绝大部分是旧书。”
相较于西门,城隍庙的旧书铺更是一个实惠的淘宝之地。唐弢回忆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时谈道:
当时上海卖旧书的地方除汉口路、福州路外,还有两处:城隍庙和老西门。这两处离我居住的地方较远,不过书价便宜,尤其是城隍庙。护龙桥附近有许多书摊,零本残卷,遍地都是,只要花工夫寻找,总不会毫无所得。因此碰到星期天或者假日,只要身边有一两块钱,我便常常到那儿访书去。
宋元明清以来民间出版业的蓬勃兴起,使得书籍的传播与流通日益大众化。而清末民初伴随机械化印刷等技术的普及运用,促成了现代出版业的发达。这一方面使图书的种类日益繁多,所面向的读者也逐渐扩展至社会各个阶层;另一方面也使得图书由过去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专属象征转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城市市民开始成为图书市场消费的主体。《创造周报》出版以后受到青年人的喜爱。“从每到星期日,在上海四马路泰东书局发行部门前的成群结队的青年学生来购买《创造周刊》的热烈,便可窥得一个梗概。”
《生活日报》的主编邹韬奋当时已经注意到报社每天贴在门口的“号外”让“数千成群的读者静悄悄仰着头细细地看着”。
在这种情形下,逛书店并非只是读书人的专有行为。当书店与书籍都进入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日常生活时,读书人如何寻找新的有别于其他阶层的行为方式以构筑其作为读书人的身份认同感?很显然,在城隍庙的旧书店、书摊前细细观摩、浏览比在四马路的书店里走马观花需要更多的闲暇时间,而且旧书店与书摊上,这些人文艺术方面的图书只有在具有一定文化积累的读书人眼里才是宝贝,在以实用技术与体力为生的普通市民眼里不过是一堆破烂。一个懂得读旧书、懂得欣赏旧书的人必定是有文化、有素养、有阅历的人。因此,知识群体通过对旧书、旧书店及书铺、书摊的歌颂来达到维护自身与其他群体相区隔的目的。这或许是尽管许多知识分子既光顾新书店也光顾旧书铺与书摊,但在他们所留下的关于书的回忆性文字中,多半是津津乐道于旧书铺、书摊上的种种趣闻以及对旧书的赞颂,而鲜见对新书、新书店的描述的一个内在原因。
本文出自《公共空间与民国上海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活建构》,有删节。原文载于《城市史研究》第34辑。作者胡悦晗,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