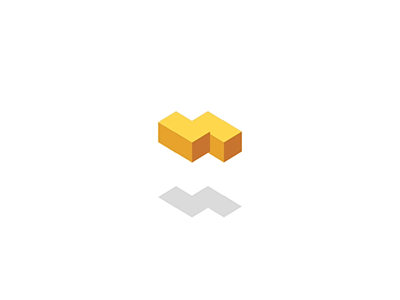在市场的摊位上看到有卖冻梨的,眼睛一亮,心里一阵狂喜,那种酸酸的味道引起某种神经反应,我咽了口唾液,一种久违的感觉让我激动不已,一幅幅画面在脑海里翻阅,那是一种儿时的记忆,也是一种奢华的回忆,既是味觉的欢乐,又是童年的伤感,冻梨不过是酸和甜的味道,却搅动了我的五味杂陈。
有多少年我已经没见到卖这种冻梨的了,这是北方的特产,俗称“冻梨蛋子”,只有冬天的时候才有,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成了不可多得的果品。一家人围坐在炉子旁边,将黑褐色的、冻得杠杠的冻梨,或放在冰凉的水里“拔”,或放在炉火上煮,去掉冰碴,这时的冻梨失去了它刚硬的外壳,看起来软软的,用热水煮过的特别饱满,鼓鼓的,嫩嫩的,包着一肚子的水,这时大人会告诉你,凉一凉,慢慢咬,猴急了会烫着的;而冰镇的看上去,瘪塌塌的,好像去了那层冰壳,便没了精神。
 ... 网络图片
... 网络图片
把冻梨放在嘴边试试,不太冰也不太烫了,咬一口,一汪酸酸的液体流入口中,酸的倒牙,酸的直流口水,酸的让你禁不住嘻哈,那种沁入心脾的酸,特别开胃,特别爽快。我更喜欢冰镇的冻梨,它酸的更彻底,更原始,更真实,保留了原有的味道,皮也比煮的稍厚一些,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进入冬至月,爸爸用自行车托回一大麻袋的冻梨,储存藏匿起来。七十年代的北方,水果极度匮乏,常见的有苹果、白梨和沙果,只有秋天果子成熟的时候才能吃到,到了冬天便很难吃到新鲜水果了,冻梨填补了这个空白,成了孩子解馋和补充维生素的唯一果品。家里孩子多,那个年代又没什么可吃的零食,如果不藏起来,恐怕几天就会一扫而光。
我们看着大人卸下一麻袋的东西,也知道是冻梨,可就不见给我们吃,我和弟弟都掂记这个让我们流口水的吃物,就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分析研究着爸妈会把它放在哪里?弟弟说:“会不会放在窖里?”我摇摇头“不可能,怕冻的东西才储存在窖里,是为了保温,冻梨怕热,越冷越好,放在窖里肯定得化了”,我说“咱们分头行动,不信找不到”。家里犄角旮旯,所有能放东西的地方我们翻了个遍,居然没有!
我站在院子里环顾四周,像个指挥官在查看地形,我想,唯一没翻找的就是煤仓,可煤都快屯到屋顶了,哪有藏麻袋的地方?那时北方的冬天是极寒冷的,零下三四十度,必须储备足够的燃煤,才能保证这一冬天的取暖。
我不服输的性格在鼓动着我,感觉那个麻袋就在那里,在那高高的煤堆上,让我去探一探。我冒着踩塌煤堆被大人发现后,暴打一顿的风险,小心翼翼,手脚并用,亦步亦趋地爬上煤堆。应该说我家的煤垛垒得很有水平,碎煤和块煤合理布局,取煤的时候既方便,又不易坍塌,否则,我这连手带脚的一顿扒拉,煤早就滑落下来,弄不好还得把我埋在下面,那时年龄小,不懂得这些,只是一门心思想着那黑黑、酸酸的冻梨何时进到我的嘴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爬到屋顶的时候,看到屋顶和煤垛之间有个空隙,一个麻袋静静地卧在那里,我眼睛放着贼光,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心想:看你还往哪里躲?我解开拴麻袋口的绳子,小心翼翼的把手伸进去,碰到冰凉梆硬的梨,我竟然感到温暖和亲切。我拿出两个,怕拿多了被大人发现,再说我只有两个裤兜,一个裤兜只能装一个,手是不能拿着的,爬下煤堆时不方便,再说拿在手上的“赃物”岂不是昭然若揭,不打自招吗?
 ... 网络图片
... 网络图片
跑出仓房,正看到弟弟们在玩捉迷藏,我兴奋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打着、闹着、跑着、跳着,玩的忘乎所以,竟然忘记了我兜里还揣着两个冻梨,随着体内温度给他的热量,两个冻梨渐渐的融化在我的两个裤兜里,弄湿了两大片。
这时大哥从屋里出来,站在哪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看,我瞬间才想起我兜里还有两个“赃物”,低头一看,两条裤腿已经湿哒哒的,我知道露馅了,装聋卖傻地说道:“裤子怎么湿了?”,大哥威严地说“兜里装的是什么?”我装傻地附和着“没有什么”,大哥说:“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我自知瞒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
大哥比我大九岁,他就代表了家长,这事让他知道,无异于和父母知道一样,我成了“贼”,不但要挨一顿胖揍,更有损于自己形象,恐怕在父母眼里我就是个坏孩子了。我求大哥不要告诉爸妈,大哥问我以后还敢不敢了?我对天发誓再也不敢了!大哥没收了我的“赃物”。我的心忐忑了好几天,父母没有问起我这件事,我才放心地翻过这一篇。但它却深深地敲打了我的心,我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不齿的事情,成为我以后生活的一个戒律,再也不去想那偷鸡摸狗的事了。
我渐渐长大之后,想起这件事,忽然有个疑问?大哥没收我的冻梨去了哪里?他不可能扔掉,也不可能交给爸妈。我恍然大悟,觉得上了大哥的当。等我后来问起大哥这件事时,他说不记得了,我瞧着大哥笑,大哥看着我也笑了。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大哥也已经离开了我。我多想让大哥再训我一顿,多想买一大堆冻梨,放在红红的炉火旁,我和大哥坐在一起,吃着冻梨,共同回忆过去的时光,苦的、甜的和酸的,可已成枉然!
如今走入市场,各种水果玲琅满目,国内的、国外的;南方的、北方的;应季的,反季的,令你眼花缭乱,吃到腻烦。谁还会选择又丑又酸,拿不到台面的冻梨?和孩子说起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好玩,更不相信我们为了一个“破”冻梨蛋子,绞尽脑汁,而冒着风险去偷来吃。他不解的说“让姥爷多买两麻袋不就行了?”,真是夏虫不可语冰!也是,现在丰富的物质生活,早已脱去了贫穷的外衣,华丽的让人无法相信,曾经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相差那么大,而这才不过几十年。我很庆幸“冻梨”成为了一种记忆,它成为我味觉盛宴的一种调剂,不再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