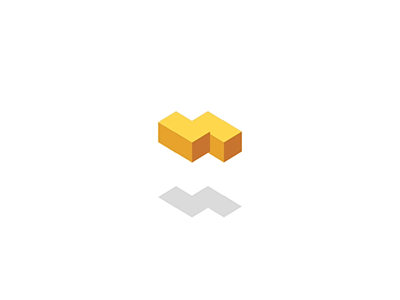...
...
沿安宁河自北向南走,临近米易县,阳光明丽起来,仿佛太阳终于揭去蒙面的薄纱。河谷开阔,植物们挂着绿叶,敛声静气,田地青青,远山逶迤。景象有点似暮春,又像初秋,让人看不够。要知道,我是从山寒水痩的青藏高原一脚踏上此地的,有点像故事里卢生在邯郸的旅店跌入梦境,脑袋中只来得及冒出一句:回到了自己的季节。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认定和钟情的季节。早春、晚秋、仲夏或者深冬,都有喜欢的缘由,以及理由。我喜欢秋天仁慈悲悯的太阳光,喜欢春天的繁花满树,喜欢夏季傍晚树枝间的飞鸟相与还,唯独不喜欢冬季那个阴沉沉的天。现在,在川南,我所喜欢的季节们都走来,组合成一个称心如意的新季节:秋天的光,春天的花,夏天的鸟语间关。
起先,我以为出现在山腰的也都是些开花的树,白色的花和柠檬黄的花缀满枝头,有人却告诉我,说那是枇杷。枇杷我见过,小小的,盈盈一握,绝不会如此肥大。求证一番,原来是罩枇杷的纸袋子。不同颜色的纸袋子,肯定罩着不同品种的枇杷。暗自想,如果有个顽童,将那纸袋子一一调换,等到采摘那一天,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然而当我站在米易真正的枇杷园,才发现偷换纸袋子的恶作剧多么不靠谱:脚下半面山坡都是枇杷树,枇杷们坐在纸屋子里,不出声,而深褐的、米白的、浅黄的纸袋子挤在枝干上,摩肩接踵,似乎能听得见彼此碰触时不耐烦的嘟囔声。
早年吃过枇杷的,以酸为主,果皮厚,一揭带一层果肉,想枇杷也不过如此。后来有一回在太湖边上吃到一种名曰白沙的枇杷,汁多而甜,让人诧异。此时蹲在米易的枇杷园里吃亲手采摘的枇杷,也甜,也多汁,感觉亲切,可亵玩。看果肉,微黄,想,也是那种叫白沙的枇杷吧。记得资料说,还有一种枇杷叫红沙。想来红沙的枇杷肯定没有白沙这样乖巧,这样透一层光,让人又想吃又不忍吃。
主人说吃枇杷要讲究,需用小木片将果子轻轻刮一遍,这样,果皮容易剥下。想当年吃枇杷,粗枝大叶,洗一洗,剥皮就吃。剥不掉的果皮,嫌麻烦,直接吃了。营养学家不是说果皮比果肉更有营养价值吗?再查资料,说枇杷果皮也可以吃,只是因为遍布茸毛,涩,吃起来既影响口感,又容易刺激肠胃,还是不吃为好。原来吃枇杷也可以不执着的,剥与不剥,全在一念。
摘枇杷,得小心翼翼。主人给了小篮子,垫软软一层薄膜,一把小剪刀。我小时候采野果,喜欢用蛮力,捏住果子一拧即可,用剪刀剪果子,不习惯,偷偷用手摘几枚。小枇杷长一层茸毛,果皮薄薄的,不敢碰,放在篮子里,仿佛将豌豆公主安放在她厚厚的床垫上。
枇杷叶革质,大而长,“琵琶弦上说相思”,想,换作“枇杷叶上说相思”也未尝不可。摘一朵枇杷花,拿在手里。白色的枇杷花被密生锈色茸毛的苞片包裹,只露出一点卵形的尖,香味却仿佛从大缸里沁出那样浓郁,每一次嗅,那芬芳似乎都来自岩石嶙峋的高山,有溪水谷风之清冽,让人怀念多年前的山间时光。王建当年写薛涛,说,“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其他倒不怎样印象深刻,唯独枇杷花里一句,让人无限想象。
写枇杷的诗词也多,“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尝滟玉蛆”“大似明珠径寸,黄如香蜡成丸”“落落金弹丸,飞鸟不敢下”“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都是金丸、金珠,质密而色浓,抛一粒出去,好像就能击中一只小鸟,但真正结在枝上的枇杷,哪有那样笨重。倒是明代杨基的那一句“南风树树熟枇杷”,因为前一句“细雨茸茸湿楝花”而使枇杷轻盈起来,显得可爱,还有辛弃疾那一句“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让枇杷自然而然,成为枇杷自己。
枇杷难保存,果皮触碰处容易坏,这使枇杷看上去仿佛有一颗敏感而玲珑的心,与之接触,不得不小心翼翼,谨慎相待。与之相反,苹果之类是果实中的顾大嫂、扈三娘,可刀枪交谈。
 ...
...
文/李万华
来源/西海都市报
责编/亚君
监制/钟自珍 总监制/薛军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立即与我们联系
 ...
...
 ...
...